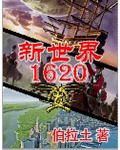有一个讲述东方政治哲学的小故事。
刚刚即位的小皇帝召见自己的老师,问朝廷怎么用人。帝师想都没想,说道:“庸才做权臣,为陛下处理国事。能人做参谋,为陛下出谋划策,监督权臣。”
小皇帝很奇怪:“为什么不让能人去掌握重权大任,仅仅是做个参谋。”
帝师笑笑:“人孰能无过,权臣位高权重,庸才难免经受不了诱惑,陛下斩了也不心疼,再换一人而已,他们只要好好执行陛下和能人制定的国策就足矣。能人稀缺,若把他们放到权臣位置上,有什么过错,要么陛下损失一位人才,要么百姓认为律法不公。”
欧洲历史也有个类似情况,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他的儿子路易十四从来不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去做财政大臣,这个位置通常都是小贵族甚至是商人出任。法国王室的包税制度实实在在地催肥了这样一批人,不过法国国王杀起来也毫不手软,什么时候觉得缺钱了,就把财政大臣抄家问罪,铁定发一笔大财。
于是有人总结出一条奇特的政治风险哲学怪论:一个有效的政治运作,不在于单纯的风险防范,而在于风险应对处理的长效和有效机制;风险通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处理风险的机制是否有效,就在于控制风险产生的成本,成本过高,注定不敢轻易处理,从而积累出更大的风险概率。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这大概就是家族企业更容易崛起,但却远比股份制企业更难长久经营的关键所在。家族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通常都缺乏有效的处置机制,任人唯亲导致的一代而衰自然比比皆是。
……
1636年1月14日,周一。
每月的第二周的周一,是国会与政府内阁例行大会,更是新年度的第一次国会、内阁和军方的集体会议,商讨当前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军事和外交议题。由于临近农历新年,大会的气氛还算轻松。
历时半年的南山总督领黑人土著暴动已经被彻底镇压。超过4000名黑人俘虏“待价而沽”,侥幸逃出生天的则被迫迁徙到更远的北方或东方,南山总督领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了好几倍。
爱尔兰战争已经进入了停战谈判的关键期,封锁泰晤士河口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依靠锡利群岛的补给便利,就连西班牙舰队都参与了进来,大量不明情况的英格兰或荷兰商船被拦截,只要再持续一两个月,英格兰就必须低头。
至于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入侵行动,目前已经形成了对峙。占领奥林达并南下累西腓港的荷兰雇佣军暂时被葡萄牙人抵挡住。但同样累西腓港也被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主力舰队继续封堵着;占据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的华美南方舰队,已经表面上占据了掐断荷兰人退路和补给线的有利位置,如今在海上也保持着和荷兰人的低强度对峙。双方就这样保持着既不宣战。也互不退让的姿态。
若干的决议在陆续表决。一声声锤声落下,但身为众议员的程大熊却次次都弃权,只是默默坐在位置上,呆呆地看着眼前桌案上的一摞文件。
有点奇怪的是,主持这么重要的国会大会的并非参议院议长包子图,而是众议院议长赵房。不光总统李萍、总理齐建军和包子图齐齐缺席。部分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没在场,倒让不少人感到一丝诡异。
“怎么没精打采的?你老婆又怀孕了?”国防部长郑泉碰了下坐在身边心不在焉的国土安全部长刘云,对对方今天莫名其妙的表现感到奇怪。
只是无言的苦笑,刘云就把视线转向了远方的众议院席位,目光落在那个同样呆滞的程大熊身上。
“苏子宁。今天有点不对。”另一边,严晓松也似乎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忍不住轻轻推了下苏子宁的胳膊。
“嗯?哪里不对了?”苏子宁从打盹中回过神,茫然地环视了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国会席上的若干空位上,“哦,几个人缺席了……应该是去参加陶心梅的葬礼了吧?这面子可大了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缺席的人都是谁……”严晓松回过头,声音压得很低,“除了包子图和总统,其他缺席的全都是国资委的人……连老齐和刘鑫今天也没来。”
这么一说,苏子宁才打起精神,开始仔细在大会场上辨识,看了几分钟后,终于慢慢点头,眉头也微微发皱。
“看来今天有大事了……”重新恢复平静的苏子宁,把身体靠在椅背上,双手环抱在胸前,似乎在想什么。
……
“……最后一个议题表决:通过和葡萄牙方面的谈判,对方正式同意以5万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出售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换取我们向荷兰西印度公司宣战。”
一番嘀咕之后,大部分议员都举手赞成,也有少部分人建议直接封锁荷兰阿姆斯特丹,不过这个意见直接被在场的海军司令王铁锤上将给挡回去了。
先不说与荷兰州长联合会的关系是否要走进一个极端,仅仅从目前海军的兵力上看已经稀释到了极限。近期加勒比海陆续发生了数起海盗出没的案件,多艘西班牙或葡萄牙商船失踪,如果不是因为华美商船速度逆天,恐怕还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
“多数票通过!所有议题表决完毕!相关决议等待参议院复审。”大会主持、众议院议长赵房一锤定音,许多议员揉着肩膀站起来,打算退场。
“大家请等下!我还有点话想说!”突然。程大熊站了起来,洪亮的声音压住了人们细碎的推椅声。
角落里,刘云的双眼突然一睁,嘴角终于出现一抹微笑。
“程大熊?”严晓松也是微微一愣,“他又要提那个‘《审计法》修正案’了?他不是已经宣布放弃了吗?”
“也许还有更重要的……”苏子宁想了想,还没有找到头绪。
程大熊在一片嘀咕声中走到主席台,从怀里摸出一本账册,轻轻放到了桌面。这个动作。顿时引起参议院席位上某个人的惊诧,那人正是国营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刘百东。
“从一开始的胆怯和迷茫,到现在的安稳生活,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和大家一样,我也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片似乎比曾经的时光更有希望、摆脱了一切恶俗的国土……”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将我所期望的幸福和美好在这个世界扎根,帮助所有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这个新世界文明的先驱或继承者……我相信这个国家可以让我实现这个理想。”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那些曾经糟糕的东西依然如噩梦般围绕在身边,我永远不可能脱离它们。我无能为力……为了我的妻子、孩子。我怂了,彻底怂了,我只能为他们虚构出一个纯净的世界……我只是一个人,我竭尽所能,也只能保护和帮助微不足道的几个身边人,我的妻子。孩子,或者邻居、同事……”
程大熊如同喃喃自语般低着头,眼泪悄然滴下,打湿了面前那本账册。
几秒钟后,程大熊猛然抬起头。举起账册,环视着下面一张张茫然的脸。从兜里掏出一把打火机,带着一丝苦笑点燃。
丢在地上的账册慢慢在燃烧,渐渐化为一团黑灰。
大门开了,总统李萍、参议院议长包子图、总理齐建军等人陆续走了进来,甚至人影中还出现了前总统陈长远、最高法官钟进山以及前参议院议长刘铭钧老人。
一番嘀咕之后,几乎所有的“非内部工作人员”都退出了大会现场,大门又悄然关闭。
“老爷子们都来了。”回想着刚才程大熊那莫名其妙的发言,苏子宁终于露出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恐怕陶心梅的死不是那么简单!”
说着,还把目光转向了不远的刘云。视线里,刘云已经闭上了眼睛,靠在椅子上打盹,平静得几乎连呼吸都快没了。
“今天,要宣布一件事,有关国资委临时成立的审计小组这半个月的工作调查报告,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烂……”走到主席台上,看了眼已经泣不成声的程大熊,包子图深深叹了口气。
台下一片寂静,有莫名其妙的,有慌张不安的,有埋头思索的,也有心不在焉的,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
……
仅仅半个月的小规模摸底调查,还未覆盖完国资委下属的所有国营集团,从几家账目上就查出了总计至少400万美元的财务漏洞,其中国营进出口集团、国营能源矿业集团、国营建设工程集团的问题最大。
超过400万美元的国营集团账上资金就这样或那样的被人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私分了,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牵扯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人。这还只是小范围的审计结果,触目惊心的数字就让包子图选择了审计工作暂停。
无非是后世用烂了的某些手段:高价采购,或是对外提供高价业务合同,或是虚报开支,然后私下获取回扣的方式吞吃国营集团资金。为此有一大批相关业务关联企业在帮助这些国营集团往外“抠钱”,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国营集团管理者本身在外的私有产业,也有不少私营大集团在推波助澜。但最终,损失都落在了国营集团身上。
至于为什么国资委会私下“不宣而查”又突然选择在今天公布结果,从刘云当场辞去国土安全部长一职,以及程大熊今天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
国防部长郑泉在报告中途是气得脸色发青,海军司令王铁锤上将直接默然退场,陆军司令陈礼文中将则起身砸烂了自己的茶杯。怒骂不止。
军方的震怒是吓傻了相当一部分的议员,不少人都面如死灰,而自觉清白的人也选择了沉默。也难怪郑泉会如此愤怒,400多万美元的窟窿,意味着8艘公主级大型轻巡洋舰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蒸发掉。每年争死争活的国防预算案,此时显得异常滑稽。
包子图时断时续地陈述,外加陆军中将陈礼文的骂骂咧咧,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钟头。
……
“……还能怎么样。谁也改不了……”
一钟头前,国会上某个众议员的“嘀咕总结”让全场陷入一片死寂,也成为了刘铭钧老人怒极攻心之后晕厥的直接催化剂。大会戛然而止,人们七手八脚地将气晕的刘老送往医院。
白雪皑皑的任家庄园,仆人们还在慢条斯理地清扫着积雪,曾经鲜艳夺目的花台已经变成了一个个装着“冰激凌”的石杯。大门外停靠着几辆马车,看样子又是一拨受到邀请的人在任家聚会。
没有启用已经大规模进入普通国民家庭的水暖供热,典雅的客厅壁炉染着点点薪火,将整个客厅烘烤得暖融融的。但和温暖的室温相比。客厅里的气氛却显得十分冰冷。一众才从医院回来的穿越众都闷闷不乐地坐着,除了壁炉里的噼啪声,就只有杨雯雯慢条斯理地打毛线的摩擦声。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初就只有那么几笔古巴镍铁矿石的生意。他们要开什么价格,我就写什么价格,反正我又没有吃里面多余的一分钱,多出的部分都回给他们了……之后他们把我从古巴进口矿石的生意上排挤掉,就没和他们往来了。”任长乐咳嗽了一声,打破了现场的寂静。对之前没有点名的事进行辩解。
“还好,那句‘谁也改不了’的奇葩言论不是你说出来的。”杨雯雯没好声气地对着丈夫翻着白眼,“平时你们两派闹得那么凶,还不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无聊……不过他们的吃相也蛮难看的。我们好歹是按着规矩在外面明抢,他们是在里面暗偷!”
“为什么改不了……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地能说出这种话?!”严晓松发出了低沉的声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钟老总结得好,在我们相当部分人眼里,这个国家是‘国家、国民和我们’三部分构成的,我们超然在国家和国民之外。”苏子宁倒是平静得很,“对,改不了,甚至因为穿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事,好的都能改坏,而且可以坏得理所当然、无可指责。”
“还是你当初说对了,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欧洲,最需要拯救的也不是大明,而是我们自己!”严晓松抓过茶几上的葡萄酒,很没有风度地直接对着酒瓶口就猛灌了起来。
“我们不求比以前做得更好,只求别比以前做得更烂。所以,我们有了个恍然先进的制度、一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制度。也许它最大的作用还不在于让我们看起来更有理想,或是让这个国家更有希望,而是约束我们的私欲,让我们即便是自私,也自私得更像个正常人,而不是自私得如脱缰野马一样肆无忌惮、贻害子孙。容易犯错的人,就不应该呆在某些位置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置内部错误的有效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死得越快,这个国家才越正常……”
苏子宁轻声说着,在场的人们都默然一片。
“刘云,你也别一副要死要活的苦肉计模样。那个陶心梅一家,是你动手的吧?你可把程大熊惹怒了啊!”任长乐撇了眼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的刘云,嘴里恨恨说着。
“随便你怎么猜……”刘云伸了个懒腰,仿佛此时已经放下了所有包袱,“我算是解脱了,以后别再有这些事来烦我。”
“老齐还没批准呢,你现在就想撂摊子,不太可能。”苏子宁拍拍刘云的肩膀,露出理解的表情,“用普通的生命,去换取我们自欺欺人的安全感……换做我,也无法拿捏到底应该怎么做,陶心梅的事其实……”
听到那三个字的名字,刘云又陷入了沉默,苏子宁也适时停住了口。
轰动曼城的陶心梅一家遇害案,最终还是定性为“歹徒持枪抢劫”,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苦涩还是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
夜深了,走出任家庄园的刘云如释重负般掏出香烟,靠在路灯旁舒服地长吐烟雾,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刘云。”苏子宁悄然出现在街边。
“呵呵,苏哥还打算兴师问罪啊。”刘云笑笑,潇洒地将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弹了出去。
“先不论对错,程大熊不是个不识大局的人,你更不是。你做得太明显了。”苏子宁静静地看着好友的双眼,似乎在寻找能穿透而入的缝隙。
“换做其他人,也许比我做得更绝。”刘云淡淡说着,似乎不太适应苏子宁死盯着自己的目光,于是略低着头从苏子宁身边错过,朝自己家方向走去。
几步之后,刘云又忽然停步回头,路灯下模糊的脸上带着异常认真的表情:“苏哥,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否则我们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要被这些人给荒废掉。他们喜欢混吃等死,你有这个闲心搭上自己去陪他们?”
“……”苏子宁没有表态,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