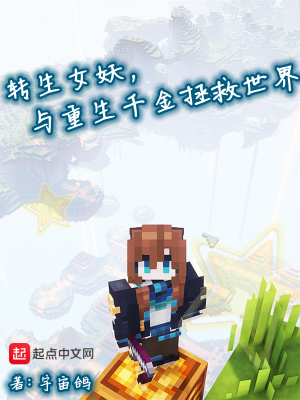秦祉不信,却也不继续追问,如今他倒觉得,摆得上与他抗衡棋局上的人,除了燕迟,就是眼前这位赵国公主了。
他觉得很有意思,燕赵联合,若又攻克了齐,他秦国要如何呢?
一向处于强国地位不动的秦国,好像要面临着一场江山风暴了。
秦祉冷薄的眸色微微变得深沉,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忐忑、惊慌与惧意。
赵怀雁道,“给花雕把毒先解了吧。”
秦祉耸了耸肩,从袖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瓶子通体黝黑,无任何花纹,半根手指的体积,很小,他把瓶子掏出来后看也不看,直接甩给了赵怀雁,说,“里面是解药,喂给她,一个时辰后她可清醒。”
赵怀雁没说谢谢,接住瓶子就朝后面的卧室去了。
秦祉不便跟上,走了。
他去看秦双。
赵怀雁来到花雕所躺的床边,曲昭跟了过来,鹰六、长虹、唤雪和蓝舞也跟了过来,金瓶馆不是只有花雕一人,这里还有很多服务客人的妓人,不过,别的馆中的妓人或许只是妓人,但金瓶馆里的妓人全是金谍网中的成员,她们深受教育,纪律严明,遇事不慌不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花雕失踪的这段时间里,金瓶馆的运营依旧毫无瑕疵。
目前守在床前照顾着花雕的是副馆主秋寅。
赵怀雁进来后,秋寅就站起身,让开床位。
赵怀雁把手中的瓶子递给她,“倒杯水来,把这解药给花雕服下。”
秋寅嗯一声,伸手接过那瓶子,先去倒水,再来扶花雕,扶花雕的时候曲昭也上去帮忙,二人合力将花雕扶起半个身子,一个人撑着花雕,一个人给花雕喂药。
药入喉后,曲昭将花雕放平。
赵怀雁坐到床沿,伸手将花雕受伤的那只手拿出来。
断指的地方没有再流血,用药物缠裹着纱布助其恢复,赵怀雁隔着一层厚重的纱布看不到断指的情况,她问曲昭,“还能恢复吗?”
曲昭道,“公主会太虚空灵指,等花雕醒了,你可试试用太虚空灵指助其长出新的指头来。”
赵怀雁听后点头,但太虚空灵指的神技她只在那天晚上与秦双的对战时意外地使了出来,后来她再尝试,就没能成功,她想到今天燕迟在书房说的话,说去楼经阁,弄明白这件事。
赵怀雁想了想,站起身,交待曲昭、唤雪和蓝舞留在这里,等花雕醒来,她带着鹰六和长虹去楼经阁。
燕迟和楼姜已经先一步回到楼经阁。
赵怀雁来的时候燕迟正在跟楼姜说圣雪城吕婴雪的成神日,并说佛广随着青海、燕乐和燕广宁一起,来了燕国,他想带赵怀雁去一趟圣雪城,问楼姜去不去。
楼姜原本是不想去的,但听说佛广也在,她就欣然点头。
燕迟见楼姜答应了,笑了笑,就问及在赵怀雁身上发生的奇怪的事,一是她能凭空御剑,二是她似乎激发了太虚空灵指的神技。
凭空御剑这事楼姜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楼危写信告诉过她。
她正欲跟燕迟说这事,赵怀雁来了。
燕迟听到外面嬷嬷的通传,薄唇抿了抿,冷冷地哼了一声,身子一仰,慵懒地斜靠在长背椅里,端起茶杯,装模作样地喝起茶。
楼姜看他一眼,笑道,“怎么,听到她要跟秦祉吃饭,心情不爽?”
燕迟挑眉,“外婆觉得我是那么小气的男人吗?”
楼姜认真地审视了一下他的表情,笑道,“不是生气,那莫非是吃醋?”
燕迟瞪眼。
楼姜笑道,“你若不愿意她去,一会跟她说就是。”
燕迟一冷哼,扭过头道,“不说,她爱去就去。”
楼姜哈哈大笑,觉得自己这个打小就冷沉低调又天赋卓绝异常沉稳的外孙从来没有过这种孩子气的较劲行为,哪里还是太子了,完全就是被心爱的女人漠视又拉不下脸来求安慰的一屁孩。
楼姜笑的时候燕迟一向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脸微微地红了红。
他大概也觉得有点丢人。
其实也没有那么生气。
但他就是不愿意让赵怀雁去跟秦祉吃饭。
这顿吃,吃的可不只是讲和。
他轻咳一声,愠怒地瞪了楼姜一眼。
楼姜忍住笑,冲门口的嬷嬷说,“把公主带上来吧。”
那嬷嬷应一声,下去带人上来。
赵怀雁上来,先跟楼姜行了个礼,又看向燕迟。
燕迟扎着头只顾喝茶,不理她。
赵怀雁也不打算搭理他,本来是要跟他打一声招呼的,他不理,她也不上前找没趣,她往楼姜坐着的矮案前走了两步,正欲开口向楼姜讨教,楼姜却忽地拄着拐杖起身,冲赵怀雁说,“我下去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赵怀雁说好,楼姜就走了。
等房门轻轻合上,赵怀雁就找了一把椅子坐。
坐了小片刻,觉得这个房间窒闷的难受,上回来都没这种感觉,这个房间宽大敞亮,又在第六楼,视野开阔,空气流通,对着天空那一面的窗户还在开着,不应该有这种窒闷的感觉才对呀。
赵怀雁蹙蹙眉头,不明白为什么。
她实在坐的难受,就站起身,去窗户边透气。
燕迟见她一直不理自己,气的将茶杯往桌上一磕,长袖一拂,起身朝她走了去。
赵怀雁听到脚步声,侧身往后看。
燕迟一脸阴沉地走过来,刚走近,赵怀雁还没来得及问一句,“太子怎么了?”那扇就架在她左胳膊处的窗户被男人修长有力的手给关住,同时关住的还有天光与云影,风与呼啸。
赵怀雁微微惊愕,刚抬头要问他做什么,一股阴影袭下来,准确无误地噙住了她的唇。
赵怀雁懵。
燕迟含住她的唇,所有的怒气、别扭和较劲都在这一刻消散。
他闭着眼睛,摁住她的下巴,把她压在窗与墙之间,尽情品尝。
其间赵怀雁挣扎过一次,被燕迟四两拨千斤地拂开。
他拥住她的腰,蛮横却又不失温柔地扫荡着她唇内的所有领地。
二人都被这霸道持久的吻逼的快不能呼吸的时候燕迟才松开她。
二人气息都微喘,脸贴着脸,鼻子贴着鼻子,叠在一起的身子撩人又爱昧。
燕迟轻轻啄着她的唇,亲昵缠棉又低沉黯哑地喊,“雁儿。”
这一句雁儿,透骨的温柔,配合着他沙哑性感的嗓音,叫的赵怀雁心尖一颤。
她伸手抵住他的胸膛,想推开她。
她实在受不住燕迟这样的攻陷,她怕她真的会沦陷。
她要逃离,燕迟却不允许她逃离,他抚着她的脸,眸色深邃地看着她,一个用力,他又扣紧了她的下巴,吻了下去。
这一回的吻依旧温柔,却充满了掠夺和占有。
吻的赵怀雁节节败退,全身瘫软在他的怀里,被他揉弄着挤进胸膛。
这样的吻让燕迟难受噪热,他隔着衣服的手蠢蠢欲动地想要撕开她,他的身体逐渐坚石更,变得极具攻击性,赵怀雁深切地感受到了,受惊地挣扎,可她越挣扎,燕迟把她压的越紧,吻的也越凶,这个时候,他不是太子,不是燕迟,他只是一个男人,一个想要得到心爱女人的野蛮男人。
他的意图头一回表现的这么明显,又这么的势不可挡,真是吓坏了赵怀雁,她一下子就哭了。
眼泪淌在二人交融的唇上,湿了唇上的热度,盐了燕迟的感管。
有点陷入甜蜜魇症里的他被这一丝盐味拉回了理智,他不再侵犯她的唇,静静地贴在那里,拥着她,努力地平复着急促的呼吸。
等气息平定下来,他缓缓把她推离了怀抱一点儿,低头看她被他吻的梨花带雨的模样,原本应该要心疼一下的,毕竟美人落泪,多么的惹人怜惜,尤其,她美的倾国倾城,虽然今天的脸做了改动,可那阴阳通吃的脸在他的轻薄下在眼泪的渲染下透着惊心动魄的诱人气息。
燕迟喉结翻滚,不想放过她,只想就这么抱着她,共赴云雨。
可时机不对,场和不对,他就是迫切的想,也只能生生地压住谷欠望。
他看着她咬着唇,被他欺负到委屈地流着眼泪的模样,只觉得幸福无比。
他皱起眉头,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而有些无力,但不可扼制的,又有一股沾沾自喜的得意显在眉梢。
他一直认为他不坏,至少,对女人,他向来不坏。
可这会儿,他只想对她坏到彻底。
燕迟移开一只放在她腰上的手,去擦她眼睑下的泪,那指腹充满龙涎香,贴在眼底的时候灼烫如火,一如他此刻滚烫沸腾的心,赵怀雁没推开他,就那么看着他,这么一刻,温馨的气氛充斥,他一手环着她的腰,一手给她认真地拭泪,高大的男人用宽阔的胸膛将她护在怀里,眸底爱意翻涌,却内敛地掩藏,等擦拭完她眼下的泪,他又将她按压在怀里,吻着她的发丝,低低地喊,“雁儿。”
这两个字从心口发出,是多么的甜蜜。
于他,是心尖的缠棉。
于她,是灵魂的呼喊。
赵怀雁无法扼制地心动了,她伸手搂上他的腰,无奈地叹一声,闭上眼睛,享受着这个男人温暖的怀抱。
燕迟眼睛发亮,对于她的接纳,简直欣喜若狂。
可他到底是喜怒无形之人,哪怕心里早已高兴的飞上了天,脸上却一点儿也不显,他紧紧箍着她,嘴角扬起愉悦的弧度。
抱了一会儿之后赵怀雁被他怀抱里的热度给闷的不行,伸手推他。
燕迟紧张地加重了力道,低低道,“再抱一会儿。”
赵怀雁不干,“热,难受。”
燕迟听着这么充满诱惑力的三个字,眸色又深邃了几寸,他黯哑着嗓音说,“我也热,我也难受。”
他拿着她手,要让她去感受他某个地方的不受控制。
赵怀雁手一缩,蓄了内力将他拍开,跑到远远的。
燕迟想抓她没抓住,他深吸一口气,摁摁眉心,将眼前的窗户打开了。
窗户一开,风就从窗口灌进来,驱散了一身谷欠望和热气。
燕迟低头整了整衣服,绕过室内的摆设,找到赵怀雁。
她正坐在椅子里喝茶,脸颊酡红,唇色菲艳,微低着头的样子看不到她眼中的流光溢彩,却能在那低头的动作里看到她的娇媚横生,燕迟脚步一顿,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她。
或许就是从这时起,燕迟知道了何为爱情。
燕迟看了赵怀雁很久,直到她受不了这样的视线,挪开茶杯,看过来,四目相对,灵魂似乎在那样的眼神对视间产生了撞击,这才有了共鸣般地错开眼眸。
燕迟耳根微红,盯着书柜的某一角,羞涩地无措。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对她,他也时不时地亲吻、抚摸,表露出他对她的势在必得,可那个时候,他压根没这种……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
忐忑,以及……无措。
忐忑?
呵。
他想,他何时忐忑过?从来没有。
而无措,就更没有了。
不管他身处何方,面对何种挑战与局势,他都没有无措过。
但今天,这两种陌生的情绪完全充斥着心房,让他甜蜜,又让他忧。
燕迟沉默地站了很久,直到按捺住心中的五彩纷陈情绪,这才缓慢走到赵怀雁的旁边,挨着她身侧的椅子坐了下去。
坐下去后,视线不受控制地朝她看去。
赵怀雁大概也有些羞涩,不知该怎么面对他,就用喝茶的动作来掩饰自己此刻七上八下的心。
心乱了,大概是动心了吧,她想。
赵怀雁蹙了一下眉头,为自己这么容易动心而感到无奈,明明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不断的欺负她,难道爱情就是在这样的欺负里产生的?
赵怀雁没谈过恋爱,更没喜欢过人,压根不知道爱情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
她喝了一会儿茶,见燕迟坐到身边了还“如胶似漆”地盯着她。
她被他盯的发毛,茶杯一搁,扭头怒过来,“干嘛!”
明明是生气发怒的话,就是不自主地掺进了娇嗔。
燕迟高兴,笑着伸手,拿起她的手捏在掌心里把玩,他不说话,只是眉目低垂,俊逸的脸上全是温柔。
赵怀雁看着他的这个样子,微愣,手都忘了抽回来。
燕迟笑道,“我们这算是互诉衷情了吗?”
赵怀雁翻白眼,“谁跟你……”
话没说完,燕迟截断她,“雁儿,口是心非不是一国公主或是一国之君的作为。”
赵怀雁咬唇,不吭声了。
燕迟拿起她的小手,放在唇下吻了一下,见她不反驳,他嘴角的笑意扩散到了面部肌肤,然后又冲进眼框,在那里掀起了涛涛笑浪。
赵怀雁气自己怂,愤怒地抽手。
燕迟没勉强,知道她对自己也动了情,这就足够了,他松开她的手,想到她晚上要跟秦祉吃饭,默了默,道,“跟秦祉吃饭的时候,我也去。”
赵怀雁一挑眉,“你不是说你不去?”
燕迟轻瞥她一眼,“你不想让我去?”
赵怀雁道,“我可没有这样想。”
燕迟道,“就算你是这样想的,我也会去。”
赵怀雁撇嘴。
燕迟又看她一眼,起身去将房间的门打开了。
打开没多久,楼姜就拄着拐杖走了进来,进来后不看燕迟,只对着赵怀雁说,“公主来找我,是有事吗?”
她说着,就往后面矮案的圃团坐了去。
赵怀雁侧身望着她,说,“是关于我身上一些迷团的,我想燕迟或者楼危应该跟你说过。”
楼姜道,“是说过。”
燕迟道,“我刚跟外婆提了,她还没来得及说,正好你来了,那就一起听听。”
楼姜刚刚出去的那段时间里又上楼翻了书,有关上古时期刀皇九央能御天下兵刃一事,所记载中,明确备注,只有拥有刀皇血脉,或是苏醒了刀皇传承之血的人才能有此惊天之能,若神血未苏醒,不管这人本身有多么的强悍,都不可能拥有刀皇的能力,那么,赵怀雁那一次的御剑之能,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她收到楼危的信后就已经翻过这类书籍,因为怕漏掉了什么,又上楼翻了一遍,但可惜,她一个标点符号都没落下,自不可能看漏书中隐藏的信息。
她摇了摇头,说,“外婆虽然读书甚广,但还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燕迟皱眉,“若连外婆都解释不清,那天下间就没人能弄明白了。”
楼姜又摇摇头,“也不能这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跟外婆一样对上古九皇之事研究多年的还有一禅叶跟佛广,一禅叶是朝圣王国的第一住持,很难见到他,但佛广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佛广进了圣雪城吗?圣雪城是巫族和灵狐的领地,这两类族类活在人间之外,也许对上古九皇的了解比我们更要深刻,去一趟圣雪城,或许会有收获。”
燕迟看向赵怀雁,问她,“要去吗?”
赵怀雁道,“若你真的能够缩短时间,那就去一趟无妨。”
燕迟笑道,“那我回去就安排。”
赵怀雁嗯一声。
燕迟想到她掌握的不太稳定的太虚空灵指,又对楼姜道,“外婆,我需要一个房间,可挡御影术隔墙伤害的。”
御影术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武学,不说学到上乘如何了,就是掌握了基本窍门,那也能杀人于无形,而基本的窍门是不需要特殊的房间来确保外界安全的,只有练至最高境界,连死物之影都能破穿或是指挥的时候才需要这么一个特殊房间。
楼姜一听,微微一惊,问他,“你想做什么?”
燕迟道,“我来对战雁儿,看她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使出太虚空灵指的神技。”
楼姜眯眼。
赵怀雁骇然,“你要找我打架?”
燕迟无语,“不是打架,是帮你快速掌握太虚空灵指的神技。”
赵怀雁不干,开玩笑,他那话的意思是他要用御影术来对战她,她打得过吗?
赵怀雁摇头。
燕迟轻笑,“怕什么,我又不会伤害你。”
赵怀雁翻白眼,“刀剑无眼。”
燕迟道,“跟你对战用什么眼睛呀,用心就行了。”
赵怀雁蹙眉,“御影术打人很疼的。”
燕迟道,“我又不打你。”
赵怀雁道,“我不信你,上回你都打了我两次,那种疼痛我到现今还记得。”
燕迟顿了片刻,迟疑地问,“真的很疼吗?”
赵怀雁道,“当然疼了,你打你自己试试。”
燕迟当真一脸严肃认真地问楼姜,“我能用御影术打自己吗?”
赵怀雁,“……”
楼姜,“……”
楼姜实在对自己这个外孙无语了,她斜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外婆怎么知道,外婆又没练过,你去太阳底下对着自己的影子打一下不就知道了?”
燕迟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楼姜抚额。
赵怀雁冲出去拉住他,“你傻了?”
燕迟看着她,慢慢伸手握住他曾经用御影术打过她的那个地方,歉意地说,“我那个时候觉得你是赵国的奸细,也存心试探你,下手就没留情,我知道自己出手有多重,你若很在意,我打回来就是了。”
赵怀雁拉住他不丢,不让他去做这种自残的行为。
她闷着声音道,“非要用御影术吗?用你别的武功。”
燕迟纠结地看着她,“御影术于我而言,是最低等的了,用别的……”
他上下扫一眼她的小身板,不想打击她,用着很委婉的语气说,“因为你的太虚空灵指能撕风控雨,抓住无形之体,我觉得拿御影术对战,最合适。”
他真的不想说,“你连我的御影术都接不住,换其它的,你怎么受得住。”
所有人认为燕迟最厉害的武学是御影术,因为天下风云榜大会上,他的成名,就靠这一绝学。
但事实上,有楼姜这样的外婆,他所学,岂能与常人一样?
燕迟的武学,远远超乎常人。
当然,他从不对外招摇,也就没人知道他的深浅,更不知他所学是哪一类,他常年佩剑,大概是剑法高手,可他腰中佩剑,从没出过鞘,元兴在的时候,他的剑就在元兴手中,闵三在的时候,剑就在闵三手中,他从不带剑,也从不玩枪弄刀,两次风云榜大会,他所用都只是御影术。
在赵怀雁看来,御影术已经算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了,他却说,最低等!
赵怀雁被打击的不行,瞪着眼睛虎视着他。
燕迟轻轻笑开,衣袂荡漾的柔情里,他附在她耳边,小声说,“别这样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