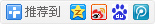马车外狂风阵阵,风从车窗灌入,吹走了车内的闷热,以及一车的沉默。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除了风声呼呼作响,很是安静,这样一来,车内的声音就显得越发的清晰可闻了,鹰老语调沉缓的问道:“老三,你刚才急着要走,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阊老靠在车壁上,缓慢的吸了一口气又缓慢的吐出来,才睁开浑浊的双眼,“只希望是我多想了,我回去好好想想,明日再告诉大哥。”
鹰老黯然的叹息:“你心思一向很敏捷,若是真的有什么怀疑的地方,明日去找京兆尹,将你的发现告诉他,能早日替老二洗刷冤屈就好。
只是没想到老二就这么走了,还是这么突然,我早上还与他说过话,没想到晚上就-----就见不到人了。”他说着说着,眼角泛起湿润,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才又狐疑道:“老二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你们可有什么看法?”
阊老和孔老互相看了看,都是摇头表示不知,孔老一脸的愧疚,“二哥早上本想让我与他一同留下来的,可我偏偏想和三个去钓鱼,钓什么劳什子的鱼,若是我没去,二哥也许就不会死于非命了。”
阊老蹙眉道:“那这么说,请你钓鱼的我岂不是更罪孽深重,更对不起二哥了?这件事我们都不想发生,可既然发生了,与其自责,不如找着凶手替二哥报仇雪恨。”
三人都陷入了沉默。车内的氛围凝重的如同清明节上坟前,天公亦不作美,像是为了映衬这事态似的。风声发出怪异的声响,好似深夜凄厉哭泣的女鬼,马车行驶了两刻钟的样子,在滕淑阁前停下来。
马夫率先跳下马车牵着马,立即有人拿着小木梯上前,扶着三老下马车,阊老故意停了停。趁机扯了扯孔老的衣袖。
等鹰老走到前面几步之后,他才靠近孔老道:“我马上要出去一趟,你替我在大哥面前圆一圆。
有一件事必须要亲自去确认。等我今晚回来后,我就去找你,这件事先暂时不告诉大哥,今夜我们商量商量。明日再做决定。”
孔老则狐疑道:“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刚才我看你就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到底发现了什么?”
阊老拧着眉道:“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你说我们这个年纪,平日都是在府里溜达,连出去的时候都不多,二哥怎么会得罪有权有势的人?
别说得罪,你我何时见他与外人发生过争执?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二哥不是最主张----你也知道。这次请浮生来府上坐,不就是为了那件事吗。”
“你的意思是-----”孔老惊恐的睁大了眼:“纸包不住火了?”
阊老无奈的摇头:“这世上哪有永远的秘密。纸本来就包不住火,能撑这么多年已经很不错了,眼看长彦娶了亲,人也长大了,还颇受皇上重视,宫家的未来,是落在长彦的身上啊。”
孔老依旧不敢置信的喃喃道:“这么说,三哥是怀疑-----”
“我还不确定,我要先去一趟宫家祠堂,如果真如我猜测的那般,那我们这么多年养虎为患,恐怕终于等到报应了。”
门口处鹰老发现二人没有跟上来,喊了声:“老三老四,赶紧进屋啊,还杵着做什么。”
“大哥-----来了,来了。“孔老招了招手,又回头看了看阊老,微微颔首后才起步朝大门而去。
鹰老见阊老重新坐上马车往别处走,问道:“他去哪儿了?都这么晚了还出去做什么?”
孔老一只脚跨进大门槛儿,一面往里面走道:“三哥说有一件事需要去亲自确认,也没说是什么,大哥别担心,我们先进去歇着。
今天你也累了一天了,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待会儿让人熬点儿鸡汤,大哥喝了再睡。”
鹰老看着院里的情形,又触景生情悲戚道:“老二虽然没了,不过他那屋儿还是给他留着,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只有这样,他若是魂魄无所依无处可去,还能有地方回。
哎----怎会遇上这样的事,我这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似乎还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只希望一切是我多想了。”
孔老安慰道:“大哥也别想那么多了,今夜先好好睡一觉,我也回屋里去了,若是有什么事,就让人来告诉我。”
“去吧去吧。”鹰老挥了挥手,两人分别回了自己的院子。
却说阊老坐马车又回到宫府,下了马车,让车夫在外面等着,自己则上前去敲门。
守门的小厮打开门一看,不解道:“老祖宗刚刚不是回了吗,快里面请,小的马上去通知老爷。”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你去歇着吧,不用管我。”阊老阻止道,径直往院里走。
小厮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没有跟上去,既然老祖宗都发话让他不要跟了,那自己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此时已经很晚了,就是下人们也好些都睡下了,阊老一路没有遇到任何人,所以毫无阻碍的来到祠堂前。
门是锁上的,阊老从袖口摸出钥匙,开了门走进屋,屋内只亮着几盏油灯,再加上那一排排黒木灵位牌,看上去阴森森的可怖。
他随手提起挂在门后的油灯就走进去,来到灵位牌前,看着架子上摆的十多个灵位牌,静静的出神。
片刻后,他才长吐一口气,放下油灯蹲在地上,在地面上一阵摸索后,最后按住一块地砖,用力一压。只听轰隆声响,再抬头,灵位架自动从中间分开。露出了藏在后面的空间,是一间小密室,只是密室漆黑一片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阊老撑着膝盖费力的站起来,提着油灯往里面走,密室内因为一点儿微弱的灯光而渐渐在眼前现出全貌来。
依旧是一排灵位架,只是上面只摆着一个灵位牌,阊老将油灯挂在墙上。拿了金标纸点燃,密室内越发亮了,可那光亮也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但即便如此,也让人看清了灵位牌上的三个字——宫承焰。
阊老双手抓住灵位牌用力往左边旋转,墙上就自动弹出一个格子,他走过去。取出放在格子内的铜制小盒子。盒子比一般的锦盒要别致的多,更奇特的是,盒子四面都上了锁。
可看到四面之中,已经有一面的锁被打开了,阊老脸色唰的一白,无力的顺着墙滑下去。
“裕德啊----孩子-----这都是报应啊,当年我和你父亲、二叔、四叔,就不该做那个荒唐的决定。报应----这都是报应。”
他哭的绝望又无助,只是紧紧抱住盒子。眼神缥缈无神,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在安静的祠堂内显得格外的响亮,一步一步,像是索命的阎王,越来越近。
阊老瞪着惊恐的双眼看着出现在密室内的身影,良久,才颤抖的扶着墙艰难的爬起来,手指着面前的人恨道:“是你-----是你杀了二哥。你这个畜生----你还是不是人,我们待你不薄,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
“待我不薄?恩将仇报?哈哈哈-----”来人笑声凄厉,语气中充满了恨意。
“你们可拿我当人看了?在你们四个老不死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卑贱的人,永远不配生活在这府上。
你们轻贱我也就罢了,可我的儿子,你们也拿他当贱奴看,你们利用完我们父子两,就想过河拆桥,就想要我父子两的命。到底是谁没人性,到底是谁欠着谁?”
暗弱的油灯下,宫承焰狰狞的面目如同地狱的罗刹,恶毒的眼中迸射出的恨意,更是惊的阊老心头发颤。
他抱紧了手中的盒子,尽量让自己不那么惊慌,而是安抚道:“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误会,我们也从没想过要你们父子两的命。
这些都是误会,我们出去,好好说话,这里是祖先们休息的地方,打扰了祖先可是要怪罪的。”
阊老试探着想要往外走,可宫曦儒却堵在门口,阴森森的笑看着他:“这才刚来,就急着要走了?祖先们可是许久不见三叔了,你也在这里多陪陪他们。
或者----干脆不要走了,反正你也没什么活头了,二叔都走了,三叔你也去陪他吧。免得二叔黄泉路上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啊。”他一步步逼近。
阊老惊惶的往后退:“你要干什么,你别乱来,现在还有机会,回头是岸,若是你再继续错下去,你就永远没有回头路了。”
宫承焰阴冷的看着他:“回头路?我早就没有回头了,本来我只想要那老不死的命,可你偏偏要自寻死路,你若是好好儿的等死,也不至于要我动手。
反正你早晚也得死了,不如就让我来替你解脱吧。”
“不-----不-----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你会天打雷劈,你会不得好死,你-----”阊老话还没说完,宫承焰的手就掐上了他的脖子。
窒息感顷刻而来,阊老双眼圆瞪,脸被涨的通红,他挣脱不了,只能用指甲狠狠去抓宫承焰的手背。
可这时候宫承焰已经没有人性,看着面前的人苦苦挣扎痛苦不已,他只觉得兴奋无比,似乎这一刻,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渐渐的,阊老停止了挣扎,眼皮也无力的耸拉着,挣扎的双手缓缓垂下去,最后脑袋一歪,空洞的双眼死不瞑目的盯着宫承焰。
“臭东西,死的都不安分。”宫承焰松开手,任由阊老咚的一声倒下去,他揉了揉手背上的抓痕,有几条痕迹已经抓的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淋。
“老家伙,死东西,活该你,感激我吧,要不是我,你就真成了老不死的了。”他又狠狠的踢了阊老几脚泄愤,然后捡起地上的盒子,又在阊老的衣服兜里找到了钥匙,才狞笑道:“多谢你送的钥匙,你放心,剩下两把,我会慢慢儿找他们要的。”
祠堂内又归于宁静,盒子被重新放入墙内,密室被重新关上,一切恢复如初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只除了地上躺着一具尚还有温度的尸体。
季老出事后,宫曦儒就让无影去查是否还有遗漏的线索,晚上无影一直未到,他不放心,就干脆哄凌依睡下后,坐在外间等着后者回来,他知道,若是无影久久未归,一定是查到了什么。
果然快子时的时候等到了,也正如他猜测的那般,无影带回了重要的线索——络牙花。
“属下将滕淑阁里里外外都找了一遍,最后在季老的屋里找到了这朵已经凋谢的络牙花,此花若是那般难以养活,必定是在京中有人种植,属下本是抱着试探的心态去看的,可没想到-----”
宫曦儒面色沉下来:“在若梦阁的花园里找到了?”
无影点头:“毕竟夫人现在被人怀疑着,属下也就想先去凌府找着,若梦阁是夫人出阁前住的地方,那里有一大片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而那株络牙就长在最高处,一眼就能看到。”
宫曦儒沉默了片刻,瞳孔突然猛地一缩,站起来道:“不好----赶紧去凌府,这络牙本就是凶手留下来误导人的,既然你能发现,京兆尹也会发现。
就算你带走了这朵花,也一定会有‘好心人’提醒他去凌府搜查。”
无影面上一凝,懊恼不已,刚才怎么就没将那株络牙给拔了,“属下这就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