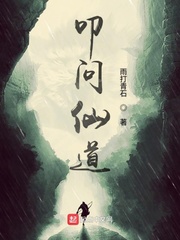就如一场大梦,偌大的青木后山百草花鸟乃至这三宗小修士俱是梦中物,而这唯独清醒的以为正是这骂骂咧咧的弄云楼老鸨子,瞧她的模样真是市井小人的脾性,一言一行哪里能瞧出先前那位一袭青衫少年的影子,可这位老鸨子分明是徐秋所扮。真真假假,一时许多人都是分不清,也有小辈言论,这徐秋本就是个女儿身,闲来无趣才是扮演了少年模样入了青水宗,更有小辈说这青木宗贼喊捉贼,分明是自家的家务事给闹得满城风雨,能说出这些话的小辈修士俱是青山宗之人,至于青木宗与青水宗是知晓的。
公羊玉本是怕这夜长梦多,欲一杀徐秋为快,谁知这小子竟是随身将自家学剑的师傅给拎了出来,关键是这马宝过还是袒护的很,明明是个男儿身,难道马宝过青木陵这些年痴傻了么?
听了公羊玉这么一句,那位徐秋拴住的马宝过忙声喝止,“莫名其妙,荒谬绝伦。”
“为师的娇妻也敢欺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么说这位妇人也算是你公羊玉半个娘。公羊玉呐,为师打小教你礼义廉耻,全都入了狗的肚子里了么,你、你这、你这是大逆不道。”
宝过老师傅,言至深处,轻咳两声,显然如今这个身子招架不住这般动怒,一旁的老鸨子二话不说,立马搀住郎君,小声轻问:“老头子,切莫与这公羊玉动气,自身这身子要紧。”
无微不至呐。
老鸨子一指公羊玉的学剑师傅,喝问青木小辈,“认得这一位否?”
马宝过的彩绘正挂在这青木殿堂之内,每日修行之时都是要拜上一拜,哪个小辈没见过?不过此间却是没有人敢应声,只听公羊玉道:“魑魅魍魉,也不晓得你这贼子用了什么手段将师傅给迷惘了心智,今日不死也难!”
一旁虞山吴来了兴致,帮腔:“定是那天池恶人楼三千的手段,否则凭借这小子的本事恐怕还不至于。杀,此子不杀,有悖天道,另外你青木宗的名声颜面可就在此一举。”
娘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公羊玉哪里不晓得虞山吴的意图,不过也没旁的办法,究根结底还是自家青木的事儿,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此事症结于此,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负个欺师的名号了。
马宝过大呼,“顽徒,尔敢!”
“公羊玉不孝,师傅如今陷入了此子的谋算之中,丢失了心智,还等徒儿将这一位给杀了,之后再请罪。”
“谋算,甚谋算?”马宝过一指公羊玉。
虞山吴接话,“马前辈,当年的风流事儿晚辈无权过问,不过这一位一定不是你当年结识的那一位,这位是个少年呐,少年所扮。”
虞山吴说过话,徐秋干脆也不藏着掖着,换回了自身的相貌,八尺少年,青衫草鞋,立身马宝过一侧,后者一愣,一时也没了主意,当即悄摸传话徐秋:“少侠,这如何是好,这不是叫老夫难办么?”
徐秋耸肩努嘴,回话:“老人家呐,自己看着办。”
公羊玉与虞山吴正等着马宝过的下文哩,只见马宝过斜视徐秋,徐秋斜视公羊玉,公羊玉与虞山吴对视,马宝过眉一横,走过徐秋来至公羊玉身前,几番张口都是无言,最后才是囫囵了一句,“为师怎么不知她是个男儿身,真当为师年纪大了,活得久了,男女都不分了么?”
公羊玉大惊失色,“师傅,既然知晓她是个男儿身,为何还称其,称其...娇妻。”
“多嘴,难道为师有这龙阳之好也要与你交代么?总之,公羊玉你今日若是帮对他出了手,就是忤逆了为师的夙愿。”
龙阳之好?
学剑的师傅与十七八的少年有龙阳之好,断袖之癖?
虞山吴长大了个嘴,罕见新鲜事呐。
三宗小辈,笑也不是,憋又憋不住。
虞山吴再是绷不住,捧腹大笑,公羊玉冷声:“虞山吴,你笑什么?”
虞山吴调稳内息,才是坐稳身形,“虞某人是受过专门的修行,一般情况是不会笑的,除非忍不住。”
说罢,又是爽朗大笑。
这会儿,倒是青木宗落了个不上不下的位置,难办的很。
俗话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一来是自家公羊穿水,一来是背负这欺师的名号,狗日的虞山吴只会说这风凉话。
背负罢。
这是公羊玉思索再三得出的结论。
骂名自身背负了,今日徐秋此子不除不可。
方才三剑已将徐秋重创,险些一命呜呼,大不了再来三剑,这小子青石剑鞘有名堂,至于师傅么,杀了之后再说,旁的一概不谈。
公羊玉眸子通红,已是下定了杀心,无论马宝过如何阻拦都是置若罔闻。稀里糊涂只听了马宝过说了一句:“糊涂呐,糊涂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唷。”
一句之后,徐秋立马揪住了马宝过的耳,“多嘴。”
这么一句,几位前辈当即一愣,难道这徐秋还有后手不成?
徐秋含首嘴角上扬微妙的弧度在那随风凌乱的碎发的下瞧的一清二楚,戏谑道:“公羊玉呐公羊玉,提剑杀我,恐怕不止是背负一个欺师的骂名唷,恐怕还有灭祖之嫌。”说罢,徐秋一提一柄拂尘,叫唤:“王鹭,何在?”
王鹭?
青木宗开山鼻祖,王鹭?
公羊玉持剑之手哆哆嗦嗦。
雪南山凝眉不下。
虞山吴一筷子猪头肉掉落。
这几位都是知晓王鹭此人,青木开山之际,王鹭可不是一个好惹之人,方圆百里可是许多姑娘遭了殃。难不成那一袭青衫能将这王鹭也给搬出来?
徐秋一句之后,只见一柄拂尘里一步一步走出了一位宽袍大袖的老儿,袖上花鸟蟒纹,与青木殿堂正中央那一位模样如出一辙,正是王鹭。扫视周遭,一望青木山水,满目疮痍呐,哪有半点当年光景,历喝:“青木宗主何在?”
公羊玉可是不敢怠慢,当即作揖行大礼,一旁的马宝过也是深深大拜,对于这位开山鼻祖,可是敬重的很。至于一旁的这位草鞋少年,脸色平静的很,什么话也不说,看这青木宗闹剧,眼角有一丝不可捕捉的狡黠,手中困鬼鞭稍微一动,草鞋随意踢动落在脚边的碎石,不经意说道:“废话莫要多说,直接问罪就好。”
这么一截困鬼鞭当真是好用,稍微一动,王鹭就是一个哆嗦,疼的很呐。其实不用这徐秋提醒,王鹭本就是对这公羊玉不待见,尤其是她这宗主之位来的莫名其妙,好端端的王氏青木,怎生成了这公羊青木,更改门庭,这是小事?另外,王鹭之子王鸠,尸骨不存。
时隔多年,公羊玉如今的本事已是返璞上游,与这马宝过大差不差,故而公羊玉方才动手之时还有些把握,可这位王鹭当年可是从这青城门下山来此,虽然与楼三千交手是个喽啰,不过这一身的归真修为,哪怕多年消耗了不少,也不是这公羊玉可以对付,所以眼下收了剑是明智之举。王鹭不依不饶,二话不说,行至公羊玉身旁,先是三个结结实实的巴掌的扇了过去,公羊玉不敢躲,三息之后公羊玉才回过神来,有些错愕,往这徐秋投去了一眼,这位少年究竟有什么本事,为何自家的开山鼻祖都能收入麾下,另外,开山王鹭为何对自身这般的不待见?
王鹭叱骂:“狗日的婆娘,胆敢青木更改门庭,究竟是哪里来的胆子。”
徐秋跺脚,“说正事!”
王鹭转身与徐秋对视,扫视其手中那一截困鬼鞭,脸色缓和了一些:“好的,少侠。”
侧身不瞧公羊玉,“这位徐秋小友与王某人乃是忘年之交,方才一幕幕王某人都是瞧见了,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徐秋摇头,“青木门规何在?”
王鹭一听这话,当即明了了徐秋的话外之意,与这青木后生吩咐道:“青木宗,当年乃是王氏的山水,奈何吾儿无本事,竟叫这公羊玉给夺取了青山。今日既然王某人在此,重立门规,将这公羊玉当即扫地出门,谁人敢言半个不字,杀之。”王鹭好歹是在这青城门待过许多年,说话做事就是比这马宝过英勇不少,一句之后,这满宗的后辈修士哪个不是墙头草,俱是起身跪拜。
说罢,王鹭拔剑就要将这公羊玉就地正法,反观公羊玉此间有如丢了魂儿一般,是如何都预料不见自身竟是落了个这个下场,自作孽不可活么?公羊玉稍微起身,将这九转玉石剑插入身旁尘土之中,将这一头的长发散开,披肩散发,扫视了在座各位,一旁虞山吴依旧是个看客,不动不言,冷眼旁观,好似此事与他无关一般。其实,虞山吴大肚之内的小算盘早是打了千百次,权衡利弊,算来算去,公羊玉身死与否,好似无关痛痒,也就没了下文。
“前辈,我公羊玉不知犯了什么罪过,更是不知为何前辈见面就是刀剑相向。杀我,不难,收回青木宗也是不难,按照晚辈的性子无论如何也是要与你殊死一搏,不过吾儿在此,也是前辈的孙儿在此,我这做娘的不好当真作个欺师灭祖之人。晚辈平生不知杀了多少人,早是预算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事已至此,还是望前辈可留穿水一命,穿水读书修行多年,对于当年往事一无所知,无罪。”
公羊玉也算是个烈女子,说罢,投眼徐秋,“昨日就不该心慈手软,一剑将你了了,也救不会如此多事。”
“大胆!”
王鹭一剑而出,直取公羊玉腹下而去。
公羊玉回首扫视一眼正昏厥公羊穿水,已是认命。
谁知,这么一剑迟迟不肯落下。
究竟如何?
那一袭青衫落在剑前,手中困鬼鞭紧紧拖拽,一剑始终不曾落下,王鹭不解,公羊玉错愕,只听前者说道:“罢了。”
王鹭惊疑,“罢了?”
徐秋一指青木一方的公羊穿水,“罢了。其实,徐某人并非是个好杀之人,无非是这青木、青山为难于我,在下才是出手,全为了自保罢了。徐秋以为,修行么,还应是修性为上,其次才是修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好比,初入青水宗,偷吃了几条灵鱼儿,要问南山宗主可知晓?定是知晓的,不过前辈并非责罚,不知者无罪么。试问青山、青木能有如此度量?恐怕是刨开肚皮也要将这鱼儿给取出吧。”
“另外,公羊穿水无罪,这话不错。徐某人时常自言自语,倘若不是这位蛮横的娘,在下与这公羊穿水应会是深交之友,谈经论道。”说罢,徐秋取出了方才公羊穿水所赠百花争艳图,抖落一番,好生瞧了许久,“在下人世走一遭,还从未遇见那位少年能有如此耐心,一笔一划百花,至于在下,不过是投机取巧,一朵牡丹罢了。”
“这一命并非是我徐某人给你留下,而是那位公羊穿水。”
说到这里,徐秋满脸光彩,从未想过自身也会有这么一天。
酣畅淋漓。
徐秋转身与这王鹭续道:“当年往事在下不知晓,也是不可妄加论断。至于,王鸠么的来去,恐怕也只有当事之人知晓,今日承蒙了王鹭前辈出手,才将这局面给打开,此事了了之后,青木往事你再好生的去考究。”
王鹭闻言,一个甩袖将这公羊玉给甩出老远,意难平的收回了剑,“秋后算账。”
后生可畏,青水宗几位老前辈当即对这位少年赞不绝口,至于徐秋究竟是如何将这马宝过与王鹭给收入麾下,不去追究,反正这小子向来都是古灵精怪,指不定从楼三千那里学来了什么本事。
南天上,白云深处,四位青城门修士,这会儿也是瞧的精彩,尤其是那位骑驴的老神仙白鹤,两眉弯弯,白须垂落,他与苦逢春对视,笑道:“时隔多年,青木此事说到底老夫也是知晓一些。上苍空有好生之德,这位小友不错呐,紧要时候还是收回了这一剑,虽说杀了也是杀了,不过这一举动,老夫甚是得意呐。”
苦逢春笑了笑,“那是自然,苦某人这些年看人可曾错过?”
一旁的姑娘花间询问,“两位前辈,还不下去救这位少年么?方才可是差些就是一命呜呼,这会儿,再对上这青石虞山吴恐怕凶多吉少。”
老人家取了一粒黢黑槟榔丢进口中,“虞山吴算不得什么,公羊玉的开天门三剑都杀不得徐秋,那么虞山吴也一定是杀不得。这位小友方才的话没有听见么,当众与这虞山吴叫骂,定是留有后手,时候不到,咱们瞧瞧先。”
白鹤一手牵着驴,另外一手一指三宗,长叹:“青城门许久都不曾管教这三宗,如今一瞧,乱了套了呐,哪有半点修士的样子,这才不过十年的光景。十年前老夫下山的时候,三宗还是祥和一片,前辈是前辈,修士是修士。”
这位年仅十七八的少年当真凭借一己之力将这青木宗的恩怨给了了且给自身留了一身的声名。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不过,这个时候,事了拂衣去还为时尚早。
三座山头,青木这一座山头的恩怨算是结算了清楚,至于另外一座山头,掌柜的是虞山吴,大肚之人,老谋深算,且在这暗处还有一位返归真中游的虞信然。从这花榜之时到了眼下迟迟不现身,仍旧藏在暗处。既然一句一个狗日的,梁子已经结下,于是,徐秋振臂高呼,“虞山吴,青木恩怨已是了了,眼下我徐秋是个无根之萍,无依无靠,与你青山之间的恩怨当是如何算,若是再不出手,在下可是要一走了之了。”
虞山吴哈哈大笑,往这芦苇尖上的贯丘元洲投去一眼,后者正对这徐秋小友有兴致的很,手段层出不穷,哪里会插手,仍是不过瘾,云淡风轻念叨:“虞山吴,莫要瞧老夫,老夫不过是个丹修,哪里有闲暇工夫茶插手?要打要杀随你的便,老夫正看的过瘾哩。”
虞山吴会意一笑,其实方才一眼哪里是为了自己而看,乃是为了那隐在暗处的虞信然问话罢了。毕竟在座之中除了这位贯丘元洲,再无旁人可敌虞信然,那位归真下游的雪南山也是不够格。
之所以,虞信然迟迟不现身,是有顾忌的,是何顾忌?
这位草鞋少年这般聪明,怎么会不知晓青山宗还有一位虞信然,既然知晓有虞信然掩再暗处,为何还是敢如此叫嚣,且与青水宗撇清了干系,当真是不怕死,还是留有后手?
不得而知。
青木宗山下已是被徐秋一剑捅了个底朝天。
虞山吴挺出腰间阔剑,正当这厮要将这一剑给吞下肚的时候,徐秋猛笑:“虞山吴,吃剑,当真不认得在下是何人了么?”
“青山小道士,可曾记得?”
虞山吴闻言小道士三个字,立马恍然大悟,“入我青山的那位天杀道士是你?”
徐秋嗤笑,“不光青山小道士是在下,青木的文弱书生也是在下。”
虞山吴脸色极其难看,自家的猪头山竟是叫着小子来去自如,还搬了一山砸落,不过后知后觉,虞山吴眉头一皱,有些古怪,那位小道士可是真有一些本事,可以瞧出这鸿蒙紫气,难道徐秋当真有这本事?
“吞剑与否,徐某人不在乎,不过猪头山你我已是交手,我徐秋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虞山吴也奈何不了我,大不了打不过溜之大吉,你这笨重的身子想要追上我,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又与青水宗撇了干系,用楼三千说话这伎俩无用。不妨,早早将你那位爹爹虞信然给叫出,否则今日想要收下我徐某人的性命恐怕就是个空谈。”
徐秋这一番话涉及了虞信然,这叫雪南山一惊,忙传话,“徐秋小有,虞信然可是归真中游,不可儿戏。”雪南山思索再三还是没将楼三千就在此地的事儿给道出,一来楼三千没有动静,二来虞信然若是出手,自身也是敌不过。
徐秋回以和睦一笑,“无妨,虞信然那个狗日的恐怕不敢出面,哪怕是出了面,也是不可奈何我,大不了徐某人将虞信然的祖上也给挖出来就是。”
“小辈,风大说话可别闪了舌头。”
风雨萧条的青木后山,一位脸色煞白的少年从这西南方缓缓行出,一身素色长袍,迈着虎步,一步堪比百步,眨眼功夫已行至徐秋五十步前。
虞信然。
归真中游,虞信然。
这也算是虞信然第一次现身在各位身前,明明有了千百岁的年纪,却是个少年身子,委实古怪,尤其是这自家小辈错愕的很,这位其貌不扬的少年就是青山老祖么?自然是不假,虞山吴毕恭毕敬的欠身行了一礼,“参见,爹爹。”一句之后,虞山吴扫视自家各位小辈,后者纷纷是起身再跪地行礼,“参见,老祖。”
虞信然并未搭理徐秋,而是与一旁的雪南山招呼,“南山道友,许久不见呐。这些年虞某人可是无时不刻不挂念青水宗的山水呐,尤其是那风波庄前的六叠姊妹瀑布,夏日傍晚乘凉吃茶可是刚刚好唷。”
雪南山打趣了一句:“挂念就去见一见呐,我雪南山从来都是个好客之人,前辈来了青水宗,晚辈还有不招待的道理么?”
虞信然含首讪笑,走了两步,一对招子老气横秋,一字一句道:“南山道友确是个好客之人,不过恐怕阁下会错了我的意思,虞某人这挂念之意可是不允同享,乃是独享。就是不知,南山道友好客能好到何等地步,能否将这青水宗风波庄借虞某人住上了十年八载?”
言外之意已是显然易见。
虞信然挂念的哪里是这山水以及六叠姊妹瀑布,而是这风波庄呐。
不待雪南山回话,一旁徐秋就是破骂:“借风波庄?”
虞信然转身看望徐秋,谁知徐秋猛道:“将你婆娘借我一用可否?届时还你一大一小。可好?”
借人婆娘,还一大一小,这是什么借?
【未完待续。】